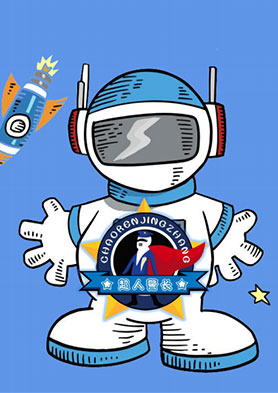哥哥的皮鞋
尘世里,有时需要的,不过是一丁点的责任、一丝缕的爱心
得到哥哥去世的噩耗,是临近春节的一个凌晨,此时的我还远在千里之外,我赶紧匆匆乘车向哥哥所在的城市奔去。
安葬了哥哥,疲倦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最后哥哥的皮鞋在我眼前定格,怎么也挥之不去。
哥哥一辈子只穿过一双皮鞋,严格说来那双皮鞋也不是哥哥的。按他当年每月32元钱工资和他平日生活的节俭,他是绝不会花上2.3元钱买双皮鞋穿的。因为父亲在鞋厂工作的缘故,一个巩姓工友委托哥哥让父亲帮着做双皮鞋结婚时穿,2块6毛钱。等哥哥休假完毕抱着皮鞋回到厂里,那位工友却因公牺牲了。皮鞋失去了真正的主人,哥哥就留下自己穿用,也成了对工友最好的纪念。要说那双皮鞋若按现在的时兴样子,一点也不美观,但因为是纯牛皮里面,纯手工制作,的确结实耐穿,再配上哥哥工人阶级的身份、中等敦实的身材,穿在他的脚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哥哥生于1930年,我是哥哥最小的弟弟,年龄差距超过20岁,哥哥也像我的父亲。以至于在外生活的几十年,每当听到《北国之春》中“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苦酒,偶尔相对饮几盅”的歌词,就特别激起我的感慨和思念。哥哥乳名叫黑牛,其实哥哥并不黑。为什么父母给哥哥取这么个名字,或许是生于苦难乱世,父母希望未来的儿子像牛一样健壮结实;抑或是因为牛生来就不惧怕艰难,从不抱怨,一直沉稳地向前走。哥哥的一生,也确实像了他的乳名,5岁就随父母下地,9岁就扶犁耕田,13岁能跟父亲一天走上百里地去拉炭。干活不惜力气,从不和父母讨价还价与弟妹比吃比穿。为了养家糊口,16岁时就到城市找活干,别人不愿干的活他干,别人不能吃的苦他吃。扛洋灰(水泥)、砸石膏、掏茅坑这些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他都干过,吃不饱穿不暖,他累得开始尿血,年纪轻轻就得了肾炎。解放后,工厂的领导看他有责任心,干活又像拼命三郎,就招他做了一名正式搬运工。还在我少年时期,家里年年都收到哥哥厂里寄来的“先进工作者”奖状。
说到那双皮鞋,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惊险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1963年阳春的一天,休假回家的哥哥借了辆自行车带我到县城看姑姑,我清楚地记着哥哥就穿着那双他从不轻易穿的皮鞋。进城的路上,要翻过两个大坡一个河湾,在拐过最后一个大坡经过河湾时,只见七八个妇女正在河里洗衣服,四五个小孩子背对着我们在路中央玩过家家。自行车靠着惯性越来越快,任凭哥哥怎么刹也刹不住,我吓得一身冷汗,就在自行车与小孩相撞的瞬间,我赶紧闭上了眼睛。“哐当”,当我睁开眼睛时,哥哥和我都被自行车重重地压在河湾边的悬崖上,自行车的前轮大半个悬在空中,不是自行车压在身上,我们哥俩非摔下河湾不可。忽然听到震响,有的小孩吓得目瞪口呆,有的则哇哇大哭,洗衣服的妇女来不及穿鞋擦手循着哭声跑来,看看孩子个个没事,才七手八脚帮着扶起我们兄弟俩。哥哥的一只手流着血,脚也被自行车蹩了一下,我的棉裤则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露着棉花。再看哥哥的那双皮鞋,一只早跌落在河湾里。哥哥摸了摸我的头,算是安慰,然后提着一只皮鞋,一瘸一拐走到孩子们身边,向家长赔礼道歉。看孩子们没事,才长长吁了口气。若干年后,我和哥哥谈起这件事,他平静地对我说:“当时那个情况,咱宁可摔成残废,也不能伤了孩子。”我在细细地想,这是不是一种责任,一种爱心?尘世里,有时需要的,不过是一丁点的责任,一丝缕的爱心,有了她就会嗅到人性的芬芳。
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我竟鬼使神差般地爬起来,在墙角边,壁橱里,鞋柜中寻找哥哥的皮鞋。找遍了各个角落也没有,我的眼睛湿润了,倒是哥哥的形象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