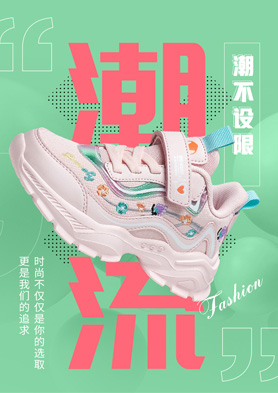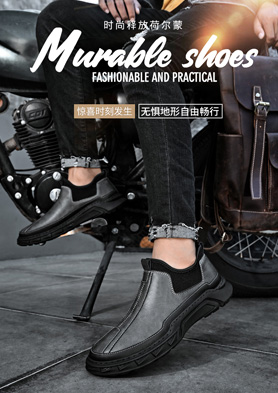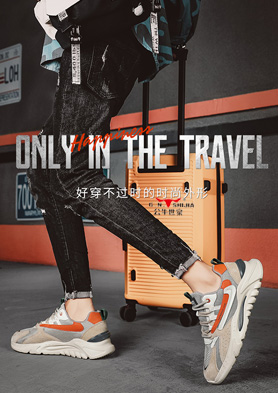春节 北京人怀念北京人
2004-04-16 11:42:23 来源: 中国鞋网 http://shoes.efef.com.cn/
“怀念”一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凸显,“每逢佳节倍思亲”。怀念好似一曲忧伤的旋律,给喜庆平添了一丝凝重……老人惦念着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孙;妻子思念着海外求学的夫君;身处异乡的北京人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出去的怀念家里的;家里的怀念出去的。怀念之情因为中国人的大节———春节的到来而愈发浓烈,其间的情愫怎一个“怀念”了得。
■留法艺术家张青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老先生的诗最能代表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
■宣武区小马厂居民刘大妈 先是儿子走了,后来是儿媳妇走了,最后孙子也走了。这心里知道孩子大了留不住,可一下子走那么远,坐飞机还得十几个小时,怎么不惦记呀!去年春节,儿子来电话说好想我,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忙告诉家里挺好,甭惦记,可你说他能不惦记吗?我们的岁数一天大一天了,!
■澳大利亚留学生李萍 我最想的是簋街上的香辣蟹和麻辣小龙虾,还有隆福寺和地安门的小吃,那些吃的又便宜又过瘾。我给老爸发了电子邮件,上稻香村给我买二斤关东糖存在冰箱里,又酸又甜又粘牙,好吃死了,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都想好了,回去天天暴撮,恶补,弄个肚歪!爱胖不胖!豁出去了!澳大利亚这边东西死贵不说,关键问题是不对味!
■首钢退休工人王大爷 纽约的夜里是北京的中午,每到星期天中午等电话成了我们老两口的规定动作,晚来一会儿都担心。“9·11”那天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直到来电话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某杂志社退休编辑老谢 去年,我和老伴上英国看儿子,住了两个来月就回来了,儿子不让回来,想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告诉他英国没豆汁,没麻豆腐。分手时小孙女抱着我们的腿不让走!
■现在新西兰经商刘玢 我在外面也算是打开局面了,想接父母过来,但他们不肯过来,他们老了,身体都不是特别好,身边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放心,夜里常被梦惊醒!
■语文教师韩迎英 平常还好说,逢年过节心里空荡荡的,虽然有孩子,可过节时家里没男人怎么也没那热闹劲儿!
■现在美国工作王苑 我最想爷爷奶奶,是他们把我看大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夜里我发烧,爷爷推着自行车,奶奶在后边扶着我去儿童医院。今年不行了,争取明年春节回去,带着女朋友,让洋妞见识见识咱北京人怎么过大节。
■回京过节,心中滋味欲说还休
王辉(美国惠普公司总部)我昨天刚回到北京。因为北京有年过八旬的母亲和岳母,我们必须回来团聚———对老人们而言,过一个年就少一个年。
我是国内最早学计算机软件编程的学生之一,开始在北京一家大科研机构工作。1986年我被公派去了一次日本,发达国家的工作、科研、生活条件让我惊讶,从此萌生了出国学习工作的念头。我爱人是“文革”前清华附中的学生,她先通过托福考试去了瑞士,就读于苏黎世大学,接着我到新加坡工作。因为那时是IT业高速发展的初期,我的工作很好找。我一步步跳槽到了惠普新加坡总部工作,后来转到美国,顺利在美定居。
离开北京十几年,孩子完全美国化了,考上了美国一流的大学,我们夫妇最大的心事完成了。但不知为何,这两年每次回来心里都有失落感。我们在美国虽有花园洋房,生活舒适,但人生成就并不大。我一直做的是最简单的售后服务工作,而我爱人因为是学机械的,竟连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干一些蓝领干的零活,为此她一直很感压抑。而我们留在国内的大学同学,差不多都是正教授级高工,学术上独当一面,成了博士或博士后导师,经常出国搞交流,有的成了几亿资金大公司的老板。说心里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羡慕北京人,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美国的北京老乡帮我找面子
建国(原美国新大陆报社社长)我生在北京,在海外过春节已有十多个年头。当报社社长时,每到春节,我联络旧金山几十个华人社团开联欢会,先是百位社会名流宴会,随后是千人舞会,州长、市长,中国总领事都出席,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老乡聚在一起,非常热闹。大家一起回忆在北京过年的事儿,有胡同的、有大院的,有哭有笑。有一次唱《我爱你中国》,全场一起跟着唱,倍儿感人,那时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爱国。
但有一点不配合,美国星级宾馆不做中国餐。点上蜡烛,侍者将西餐甜点一道道上来,挺高雅,但有点不伦不类。过年时,我们北京老乡一般不和那些中国城里讲广东话的老侨们在一起,我这报社的却要跟他们联系。他们其实更实惠。在五颜六色,摇摇欲坠的百年会馆老楼里大摆宴席,食客有黄有白有黑,大吃大嚼龙虾和“咕老肉”。
有位黑人小伙,蹭饭不说,还顺手捎走一副精美的中国筷子。GOOD LUCKY TO YOU!(祝你好运气)我恭喜道。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尼克松访华,国内有些报刊说,随行的黑格将军在中国主人的国宴上偷了个小酒杯。你看,美帝国主义贪婪而丢人!
过年了,大家都特爱看中国的文艺节目。前几天,我和一大堆老中老美在电脑上看哈佛同学的中国舞表演,小学级水平,教授级面子(说出这话我去哈佛最好绕着走)。完了还放映中国名片,有七八十年前的左翼电影《新女性》,外加《黄土地》!
有位北京来的女生因为《卧虎藏龙》扬眉吐气。但看《黄土地》时,周围美国同学不时怪异地看她,于是乎她手心开始发汗了,倍儿希望好看和紧张在后头。边看边问我,“这电影没台词?”我说,“大概吧,不过很有名。”“你看过吗?”她也开始用怪怪的眼光审视我。“没有。”老实说,在国外,大家的自尊心都特别敏感,过年时更是这样。容不得一点对祖国不利的事儿。
第二天,我自不量力,把我刚拍的古装电视剧《古董王爷》拿去给同学看,希望给咱们中国人挣点面子,但南方说太京味,北方说太海派,妈妈不疼,姥姥不爱,闹得我不尴不尬,还是咱北京人护着咱北京人,他们都跟着一起吵吵,说“好玩”,于是外国人也跟着咧着大嘴笑了,说good。
事后我感谢大家,咱北京人为中国人找回了面子,没白过这个春节。
■想念炸酱面
黄智子(原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驻澳记者,翻译兼教师)在新东安市场还叫东安市场的时候,每年春节前,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去逛老东安市场的场景,成为我梦中永恒的主题:冬天的傍晚,下着小雪,柔和的路灯,顶着搪瓷的灯伞摇曳在木电线杆儿上,景色如纽约落雪中的圣诞夜景,一样温馨。我们一路由父母在前拽着,滑犁耙似的溜到八面槽……回家前,父母总会在东安市场稻香村点心柜台上买两块点心,用两小张粗糙并且偏黄色的点心纸托着,允许我们先吃上再回家。
那常规性的两块点心,无意中记录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北京人生活水平的变迁。我记忆中,开始我们常吃到奶油花儿装饰、带果酱层的蛋糕,先小心翼翼地舔去奶油花儿,然后再吃蛋糕,幸福极了。后来就改槽子糕了,就是今天的蜂蜜蛋糕,浮头儿上带葵花籽仁儿,也好。再后来,是父母手头紧了,还是他们变口味了,反正给我们姐弟俩改牛舌饼、江米条,小圆鸡蛋饼干了……最后就变成果子面包掰两半啦。那也还是好。因为父母的心在,什么都好!
类似这种童年埋下的饮食习惯和记忆,让人不管在外住多久,真正想吃的还是鸡蛋西红柿打卤面,大碗儿炸酱面,馋的还是北京的带刺黄瓜,烤鸭和鸭架汤,六必居的小酱菜,豆浆油条和油炒面……
■过年的事儿
邓伟(摄影家)不论游走海外还是身在北京,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北京过年的事儿。
好多年前,我上中学时,周末常去李可染先生家。那时候,逢到过春节,做裱糊匠的姑父总会笑眯眯地来找我,他手里一准儿提着一个糊得漂漂亮亮、一米来长、大红的鱼灯笼。他知道,又到了我往可染先生家送鱼灯笼的时候了。
三姑父的好手艺,我挺喜欢。提着他糊的鱼灯笼走在街上,我的手总是抬得高高的,特别小心。怕上公共汽车挤坏了灯笼,索性提着灯笼从新街口走到三里河可染先生家。要知道,这灯笼市场上可寻不着,只有巧手的姑父才糊得出来。
记得每回到了先生家,他也老早等着似的,马上接过灯笼,挂在画室的门框上。可染先生说过,每次见着鱼灯笼,就觉得有了过年的意味了。
■一到春节,就特别想北京
方维华(瑞典隆德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大学毕业后考了首都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到瑞典隆德大学读博士。我爱人是学中医的,也陪读去了,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隆德,说了一口瑞典语。
当时不知为什么就那么想出去,其实出去学习很不容易。我一人的奖学金要3个人用,因为没路费,我们整整5年没回北京。在隆德,一到春节,就特别想北京,想北京人过节的那个喜庆劲儿,可瑞典人不管这个,无人和我们分享节日的快乐。
这几年我年年回京过春节,眼见北京的变化越来越大,学习和科研的条件越来越好,人才的价值也越来越高。母校的研究所早成立起来了,所长是个比我年轻得多的留学归国人员。看着他在工作中挥洒自如,手里有大笔经费,开展不少研究项目,而我在瑞典永远是个小萝卜头儿。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做的,但发表论文时我的名字永远在最后一位……
昨天一下飞机,在机场见到了我的校友,我们热烈拥抱,我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北京啊,如果我早些回到你的怀抱,我的人生也许不是这样……
■留法艺术家张青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老先生的诗最能代表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
■宣武区小马厂居民刘大妈 先是儿子走了,后来是儿媳妇走了,最后孙子也走了。这心里知道孩子大了留不住,可一下子走那么远,坐飞机还得十几个小时,怎么不惦记呀!去年春节,儿子来电话说好想我,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忙告诉家里挺好,甭惦记,可你说他能不惦记吗?我们的岁数一天大一天了,!
■澳大利亚留学生李萍 我最想的是簋街上的香辣蟹和麻辣小龙虾,还有隆福寺和地安门的小吃,那些吃的又便宜又过瘾。我给老爸发了电子邮件,上稻香村给我买二斤关东糖存在冰箱里,又酸又甜又粘牙,好吃死了,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都想好了,回去天天暴撮,恶补,弄个肚歪!爱胖不胖!豁出去了!澳大利亚这边东西死贵不说,关键问题是不对味!
■首钢退休工人王大爷 纽约的夜里是北京的中午,每到星期天中午等电话成了我们老两口的规定动作,晚来一会儿都担心。“9·11”那天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直到来电话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某杂志社退休编辑老谢 去年,我和老伴上英国看儿子,住了两个来月就回来了,儿子不让回来,想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告诉他英国没豆汁,没麻豆腐。分手时小孙女抱着我们的腿不让走!
■现在新西兰经商刘玢 我在外面也算是打开局面了,想接父母过来,但他们不肯过来,他们老了,身体都不是特别好,身边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放心,夜里常被梦惊醒!
■语文教师韩迎英 平常还好说,逢年过节心里空荡荡的,虽然有孩子,可过节时家里没男人怎么也没那热闹劲儿!
■现在美国工作王苑 我最想爷爷奶奶,是他们把我看大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夜里我发烧,爷爷推着自行车,奶奶在后边扶着我去儿童医院。今年不行了,争取明年春节回去,带着女朋友,让洋妞见识见识咱北京人怎么过大节。
■回京过节,心中滋味欲说还休
王辉(美国惠普公司总部)我昨天刚回到北京。因为北京有年过八旬的母亲和岳母,我们必须回来团聚———对老人们而言,过一个年就少一个年。
我是国内最早学计算机软件编程的学生之一,开始在北京一家大科研机构工作。1986年我被公派去了一次日本,发达国家的工作、科研、生活条件让我惊讶,从此萌生了出国学习工作的念头。我爱人是“文革”前清华附中的学生,她先通过托福考试去了瑞士,就读于苏黎世大学,接着我到新加坡工作。因为那时是IT业高速发展的初期,我的工作很好找。我一步步跳槽到了惠普新加坡总部工作,后来转到美国,顺利在美定居。
离开北京十几年,孩子完全美国化了,考上了美国一流的大学,我们夫妇最大的心事完成了。但不知为何,这两年每次回来心里都有失落感。我们在美国虽有花园洋房,生活舒适,但人生成就并不大。我一直做的是最简单的售后服务工作,而我爱人因为是学机械的,竟连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干一些蓝领干的零活,为此她一直很感压抑。而我们留在国内的大学同学,差不多都是正教授级高工,学术上独当一面,成了博士或博士后导师,经常出国搞交流,有的成了几亿资金大公司的老板。说心里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羡慕北京人,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美国的北京老乡帮我找面子
建国(原美国新大陆报社社长)我生在北京,在海外过春节已有十多个年头。当报社社长时,每到春节,我联络旧金山几十个华人社团开联欢会,先是百位社会名流宴会,随后是千人舞会,州长、市长,中国总领事都出席,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老乡聚在一起,非常热闹。大家一起回忆在北京过年的事儿,有胡同的、有大院的,有哭有笑。有一次唱《我爱你中国》,全场一起跟着唱,倍儿感人,那时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爱国。
但有一点不配合,美国星级宾馆不做中国餐。点上蜡烛,侍者将西餐甜点一道道上来,挺高雅,但有点不伦不类。过年时,我们北京老乡一般不和那些中国城里讲广东话的老侨们在一起,我这报社的却要跟他们联系。他们其实更实惠。在五颜六色,摇摇欲坠的百年会馆老楼里大摆宴席,食客有黄有白有黑,大吃大嚼龙虾和“咕老肉”。
有位黑人小伙,蹭饭不说,还顺手捎走一副精美的中国筷子。GOOD LUCKY TO YOU!(祝你好运气)我恭喜道。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尼克松访华,国内有些报刊说,随行的黑格将军在中国主人的国宴上偷了个小酒杯。你看,美帝国主义贪婪而丢人!
过年了,大家都特爱看中国的文艺节目。前几天,我和一大堆老中老美在电脑上看哈佛同学的中国舞表演,小学级水平,教授级面子(说出这话我去哈佛最好绕着走)。完了还放映中国名片,有七八十年前的左翼电影《新女性》,外加《黄土地》!
有位北京来的女生因为《卧虎藏龙》扬眉吐气。但看《黄土地》时,周围美国同学不时怪异地看她,于是乎她手心开始发汗了,倍儿希望好看和紧张在后头。边看边问我,“这电影没台词?”我说,“大概吧,不过很有名。”“你看过吗?”她也开始用怪怪的眼光审视我。“没有。”老实说,在国外,大家的自尊心都特别敏感,过年时更是这样。容不得一点对祖国不利的事儿。
第二天,我自不量力,把我刚拍的古装电视剧《古董王爷》拿去给同学看,希望给咱们中国人挣点面子,但南方说太京味,北方说太海派,妈妈不疼,姥姥不爱,闹得我不尴不尬,还是咱北京人护着咱北京人,他们都跟着一起吵吵,说“好玩”,于是外国人也跟着咧着大嘴笑了,说good。
事后我感谢大家,咱北京人为中国人找回了面子,没白过这个春节。
■想念炸酱面
黄智子(原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驻澳记者,翻译兼教师)在新东安市场还叫东安市场的时候,每年春节前,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去逛老东安市场的场景,成为我梦中永恒的主题:冬天的傍晚,下着小雪,柔和的路灯,顶着搪瓷的灯伞摇曳在木电线杆儿上,景色如纽约落雪中的圣诞夜景,一样温馨。我们一路由父母在前拽着,滑犁耙似的溜到八面槽……回家前,父母总会在东安市场稻香村点心柜台上买两块点心,用两小张粗糙并且偏黄色的点心纸托着,允许我们先吃上再回家。
那常规性的两块点心,无意中记录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北京人生活水平的变迁。我记忆中,开始我们常吃到奶油花儿装饰、带果酱层的蛋糕,先小心翼翼地舔去奶油花儿,然后再吃蛋糕,幸福极了。后来就改槽子糕了,就是今天的蜂蜜蛋糕,浮头儿上带葵花籽仁儿,也好。再后来,是父母手头紧了,还是他们变口味了,反正给我们姐弟俩改牛舌饼、江米条,小圆鸡蛋饼干了……最后就变成果子面包掰两半啦。那也还是好。因为父母的心在,什么都好!
类似这种童年埋下的饮食习惯和记忆,让人不管在外住多久,真正想吃的还是鸡蛋西红柿打卤面,大碗儿炸酱面,馋的还是北京的带刺黄瓜,烤鸭和鸭架汤,六必居的小酱菜,豆浆油条和油炒面……
■过年的事儿
邓伟(摄影家)不论游走海外还是身在北京,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北京过年的事儿。
好多年前,我上中学时,周末常去李可染先生家。那时候,逢到过春节,做裱糊匠的姑父总会笑眯眯地来找我,他手里一准儿提着一个糊得漂漂亮亮、一米来长、大红的鱼灯笼。他知道,又到了我往可染先生家送鱼灯笼的时候了。
三姑父的好手艺,我挺喜欢。提着他糊的鱼灯笼走在街上,我的手总是抬得高高的,特别小心。怕上公共汽车挤坏了灯笼,索性提着灯笼从新街口走到三里河可染先生家。要知道,这灯笼市场上可寻不着,只有巧手的姑父才糊得出来。
记得每回到了先生家,他也老早等着似的,马上接过灯笼,挂在画室的门框上。可染先生说过,每次见着鱼灯笼,就觉得有了过年的意味了。
■一到春节,就特别想北京
方维华(瑞典隆德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大学毕业后考了首都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到瑞典隆德大学读博士。我爱人是学中医的,也陪读去了,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隆德,说了一口瑞典语。
当时不知为什么就那么想出去,其实出去学习很不容易。我一人的奖学金要3个人用,因为没路费,我们整整5年没回北京。在隆德,一到春节,就特别想北京,想北京人过节的那个喜庆劲儿,可瑞典人不管这个,无人和我们分享节日的快乐。
这几年我年年回京过春节,眼见北京的变化越来越大,学习和科研的条件越来越好,人才的价值也越来越高。母校的研究所早成立起来了,所长是个比我年轻得多的留学归国人员。看着他在工作中挥洒自如,手里有大笔经费,开展不少研究项目,而我在瑞典永远是个小萝卜头儿。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做的,但发表论文时我的名字永远在最后一位……
昨天一下飞机,在机场见到了我的校友,我们热烈拥抱,我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北京啊,如果我早些回到你的怀抱,我的人生也许不是这样……
中国鞋网倡导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烦请第一时间与我们联系,谢谢!也欢迎各企业投稿,投稿请Email至:403138580@qq.com
- 上一篇:你的主页为何落雪无声
- 下一篇:50岁的女人,夏天试试下面这四双鞋子,好看又时髦
我要评论:(已有0条评论,共0人参与)
你好,请你先登录或者注册!!!
登录
注册
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