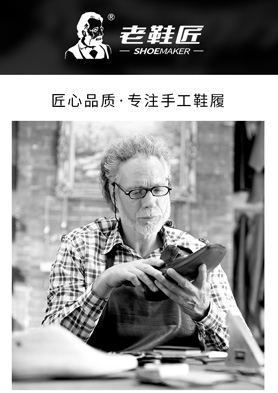补鞋匠望子成龙 准学子苦盼贵人
7月24日下午3点,赵毓龙接到了长春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给记者打来电话,请求本报一定呼吁呼吁,让“贵人”帮他实现大学梦。
他的条件是,“我愿意无偿用毕业后的四年,回报热心人的救助”。
19岁的赵毓龙,自小跟着补鞋的父亲流浪求生;父亲不识字,但识大体,一直苦供子女读书,岢岚、兴县、河曲,赵毓龙四处借读。一台流浪的补鞋机,帮一家人换来了房租,也换来了赵毓龙优异的成绩和大学通知书。
但是,若无“贵人相助”,他的大学梦可能再次破灭。
7月15日,本报编辑部收到一封求助信。
写信者叫赵毓龙,是河曲县文昌中学高中毕业生,老家在河曲县社梁乡军池村。
信中说,去年高考他考了490分,虽然考取了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只能放弃;今年,赵毓龙又考了577分,但和去年一样,学杂费仍然交不起。“那张大学毕业证,对我来说可能只是梦想。妈妈多病,常年在家卧床;爸爸靠着一台补鞋机到处流浪,换取每月三四百元的微薄收入,可这连吃饭租房都不够,根本不可能凑起来每年五六千的大学学杂费”。
赵毓龙“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去年考取的是什么学校。去年9月,在文昌中学师生们的帮助下,赵毓龙免费重新回到了高中校园。“从去年那天开始,我便下定决心,如果再有机会考取大学,我就用自己的青春作抵押,报答帮我上完大学的贵人。希望你们在方便的时候,帮我呼吁一下”。
记者决定见见他们。没想到,这场采访几乎也成了一场“流浪”。
没人住的家
7月16日下午,忻州市河曲县。
颠簸了几百公里,终于来到信中提及的社梁乡军池村,一个典型的晋西北贫困山村。向村民打听赵毓龙,得到的回答是“没这个人”。“刚考上了大学,他父亲是补鞋的”。在记者的提示下,一位姓窦的村民恍然大悟,“你说练锁家呀,孩子们一个比一个争气,可惜就是家里穷”。
村民说的“龙龙”,正是赵毓龙。但是,村民说“那孩子从小就没在村里呆过”。
原来,赵毓龙的父亲赵练锁幼年不幸,2岁丧父,6岁丧母。从小,赵练锁就在内蒙古的巴彦卓尔盟、临河市和我省的岢岚、兴县、河曲等地流浪,下煤矿、做毡垫,最后选择了补鞋。
后来,赵练锁在岢岚县认识了一位当地女人,在那里成了家,还有了孩子。但是,一家人始终跟着补鞋摊流动度日。
村民指着村中靠山的一处窑洞,“瞧,那就是练锁家”,“实在是不算个家”。
这是一间破旧的窑洞,多年无人居住,门口的荒草一人多高;雨水顺着窑顶冲出的沟痕一道道清晰可见;窑洞的门窗早成了斑驳的烂木头……
村民们只知道,赵练锁一家在岢岚也过得很艰难,“租房子住”。赵家连吃穿都难以维持,“河曲这面的乡亲们去看他们时,这家带点吃的,那家带件旧衣服”。“我们这儿,吃百家饭穿千家衣,为的是命硬的孩子好成活;可对龙龙,却只是为了能吃饱穿暖”。
争气的孩子
求助信中称,赵毓龙在河曲县文昌中学读高中。但是,这里放了暑假。
学校值班人建议记者去找柳根海,河曲县原教育局局长。柳和赵练锁沾着点亲,很了解赵毓龙的情况。
找到柳根海家没费劲。柳根海说,“那孩子的学习没得挑剔,但实在是家庭条件太差”。
柳根海介绍说,在高中期间,赵毓龙除了上学,还承担起了帮父亲摆摊、收摊的任务。“每天早上,他5点钟便必须起床,和父亲一起搬运补鞋用的工具、材料;中午下课后,别的同学吃饭去了,他还得赶到父亲的摊点上,煮点挂面,和父亲一起共进午餐”。
中午,补鞋人一般不多。赵练锁喜欢在鞋摊上靠着工具睡会儿,而“龙龙则不管冬天、夏天,手中总是夹着本书”。
刚在河曲上学时,赵毓龙在学校上过灶,“早餐是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就是一份白大米,不吃菜,喝点白开水”。
尽管如此,一个月后赵毓龙还是退了灶,和父亲一起到街头吃饭。
他是不愿一天多花2元的饭钱。
赵毓龙上学,从来没有买过笔记本、练习本。“上学用的作业本,没有办法,必须买;但第二年,孩子就在去年的作业本背面做笔记”。
2005年暑假,柳根海邀请赵毓龙在家里住过三天。“来之前,我让孩子带几件换洗衣服,可赵毓龙却大本小本拿了十多本书;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在阳台上读英语;晚上大家都睡了,他房间的灯还亮着。
柳根海说,赵毓龙不习惯他家的书房,“总是爬在床上看书、做练习,每天都到深夜12点”。
补鞋的老父
继续四处打听。
7月18日上午10点,几经波折的记者终于发现目标:到处流动补鞋的赵练锁。
这里是偏关县通往河曲县的旧街十字口。远远的,便看见一个弓着背、瘦弱的身影。
这是一个老者,眼窝深陷,爬满细细皱纹的脸,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
老者的身边,是一台擦得发亮的补鞋机,还有整齐排列的一些补鞋工具。
“我就是赵练锁”。
“龙龙一早6点帮我把摊子安顿好,便回家了;我知道录取结果马上出来了,给了他1元钱,让他8点后到附近的网吧查查;可他说没必要花钱,结果迟早会知道的”。
赵练锁抽旱烟,很劣质的那种,极呛。“抽烟的烂毛病一直想戒,可累了也能解解乏。唉,一年得五六十块钱呢”。
赵练锁说,儿子赵毓龙上学以来,成绩一直很好。“2005年,我老婆的腰忽然疼得厉害,再也不能干活;那一段时间,已经高二的龙龙成绩忽然下来了,从班里的前一二名降成了倒数几名”。
谈着这些,赵练锁低头抽泣起来,“我第一次动手打了孩子”。后来,赵练锁才知道,许多考试题赵毓龙都会,但为了辍学才专门做错。
“孩子知道要是主动提出不上学,我们不会同意;只有成绩不好,我们才会安心地让他早点回去打工养家”。
“我穷,是因为没文化”,“不想让孩子再过这样的日子”。
期待贵人
7月18日下午3时,河曲县文笔镇坪泉村,赵练锁租住的小院。
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靠西的三间平房已经倒塌,屋顶的椽梁裸露着;北面的正屋也已破旧不堪,被分成两部分,靠东的两间被赵家租住,“每月50元”。
终于见到了赵毓龙,小伙子从屋内迎出来,礼貌地问好。
屋内的顶棚露出一根根椽子;还有一半用塑料布遮着,算是吊顶。
这个家里惟一的电器,是炕上墙壁上吊着的一个小电风扇。赵毓龙说,那是父亲前几年在附近的一家电厂捡来的。
像样的家当,是一高一低两张桌子,也是用捡来的木头钉起来的,赵毓龙和二姐每天晚上回家,就在这两张桌子上补习功课。
屋顶上,挂着两个灯泡,一个是10瓦,一个40瓦。赵毓龙和姐姐做功课时,就打开40瓦的;而平常,一家人只用那个10瓦的。
赵毓龙有两个姐姐;由于家贫,学习成绩优良的大姐早早离开了学校,到榆次区打工;二姐赵玉梅和他一起参加了今年的高考,考了466分。
赵毓龙自小随父母在岢岚县生活;初中时,赵毓龙又随父母在兴县生活。“今年在这儿住,明年又得找别的房子住;我们还得给学校交借读费”。“也想过给孩子们买个房子,哪怕很小的那种,不要这样到处流浪”,赵练锁说。但“最少也得几万”的购房款,不是他们这个“流动补鞋家庭”能够承受的。
赵毓龙念完初中后,赵练锁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河曲县城,在离城4里多的坪泉村住了下来。
上学多年,赵毓龙几乎每年都是班里的优秀生、三好学生。赵练锁从家中的一只纸箱底上找出两个崭新的笔记本:一个是儿子2002年参加数学竞赛的奖品。一个是儿子2006年度三好学生的奖品。赵练锁说,孩子几年来一直舍不得用,说要等上大学时用。
说起了上大学,赵毓龙算开了账,父亲钉一双鞋,多的2块,少的5毛1块,“光一个月50元的房租,就得钉最少30双鞋”。
如果要上大学,一年需要五千元学杂费和最少三千元的食宿,“父亲得钉五千双鞋”;加上母亲看病等家中开销,“一年父亲钉不够两万双鞋,根本无法维持。
赵毓龙一有空,便到父亲的摊子上帮着招揽生意、做些小活。可是,一天下来,最多来补鞋的也就十多二十个人。“我对不起孩子,没有能力让他们继续上下去”,赵练锁哭了。
“爸爸,我为你自豪”,“林肯总统、朱可夫元帅、作家安徒生,他们都是补鞋匠的孩子”,赵毓龙安慰父亲。“只要有人愿意帮我上大学,我毕业后愿意用四年的免费工作去还他们的资助”。
说着未来的打算,挂着泪花的赵毓龙一脸坚强。“我在期待着贵人早日出现”。
- 上一篇:鞋儿不破帽儿不破“济公新传”颠覆济公
- 下一篇:离职前起贪念 盗窃产品鞋被批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