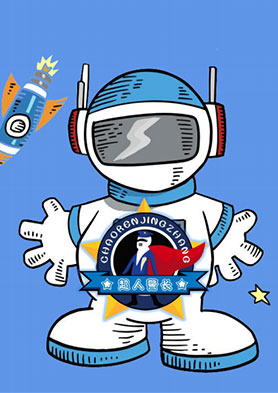一个关于男人和鞋子的故事
周末在家里收拾房间,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整理鞋子,整理那堆满一堵墙各式各样的三十多个鞋盒,鞋盒里装的靴子、单鞋、凉鞋、高筒的、低跟的、白色的、红色的……。我没有收集鞋子的癖好,但每每看见漂亮的鞋子,都有种欲罢不能的冲动。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穿上最适合的鞋子,走出自己的人生。所以很多年以来,对于鞋子,我总有割舍不下的情缘。衣服可以随便穿,但是鞋子一定要最舒服的。即使破损我也会找最好的修鞋店来修理我的鞋子。因为我一直相信每个女人都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水晶鞋。
但每次看见鞋子,尤其是修补过的鞋子,总让我不经意间想起一个男人,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他的摊子就摆在单位门口的弄堂里,那是我每天上班经过的地方。早早就看见他在修补鞋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记得那天的雨很大,那双白色圆头的单鞋突然掉了鞋跟。因为要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不得已去了他的小摊,在弄堂的拐角处。与其说这是一间砖瓦房,不如说是两间房子之间的缝隙搭建的临时棚。狭窄的空间没有窗户。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屋子里也总是沉浸在一片漆黑里。
他用的还是那最原始的修鞋机,用手轻轻的摇动滑轮,带动那根满是油渍的皮带,麻线随着针头在鞋面上上下不断游走。这种修鞋机已渐渐被当下开满街头巷尾专业修鞋店里崭新的修鞋机器所取代。这种最原始的修鞋技术也显的格格不入了。看着他专注的样子,我开始打量起这个外乡人。满是污垢的指甲,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我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岁了,30,或许20,外乡人看起来总是比实际年龄不符。
我撑着伞站在他的门口,他见我没有进来的意思,笑着跟我说:屋子小,让您淋雨了。说着还搬了张干净的凳子给我。对于这样的人,我没有任何鄙视的成分,但我们都习惯了,习惯了高人一等,习惯了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别人,也习惯了用一种势利的眼光来察言观色。我们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一样为了一日三餐,一样为了努力成为一代房奴。除了比他们活得光鲜一点,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值得高傲的。
他很快帮我修好了鞋子,还仔仔细细端详着,拿了条毛巾帮我把鞋子里里外外擦了一遍,递给我。他的手艺很不错,丝毫不逊色于专业的修鞋连锁店,却只收我2块钱。
每次经过他的小摊,都只看见他一个人专注的修鞋。他手上的鞋多是些附近居民穿旧的鞋子,舍不得扔掉,便拿到这里来修补。第二次去他小摊,是接近傍晚的时候。这一次我走进了他的小屋,光线很昏暗,他还是很认真的帮我修鞋,一边对着屋里说:饭菜我都烧好了,你记得趁热吃。屋子小的一目了然,但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只看见墙角放着一排气球。想起平时晚上加班回家,路过南站天桥时,总是看见摆摊打气球的身影。
里屋的房门打开了,这是另外隔出来的,除了一张床,屋里已经摆不下任何东西了。一个女人穿着一间很短的吊带睡裙走出来。女人不漂亮,但指甲油很鲜艳,她啃着黄瓜,半靠在床头,听着收音机。男人很关切的说:洗澡水放着吧,我来倒,你先吃饭吧。女人继续修补着她美丽妖艳的指甲,根本没有理会他。
在我印象里,他更适合找一个安分守己的下乡女人,可以不漂亮,但可以跟他一起吃苦耐劳,一起同甘共苦。从那以后,我每次路过的时候,他的小屋都是房门紧锁。再后来,他在弄堂的另一端落了户。这间房不是很好,但的的确确属于砖瓦房了。与他原来那间相比,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但是那个女人我没有再见过。
- 上一篇:西洪路有位“牛”大叔
- 下一篇:战疫·秀洲丨小红鞋完成了使命 但抗击疫情的脚步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