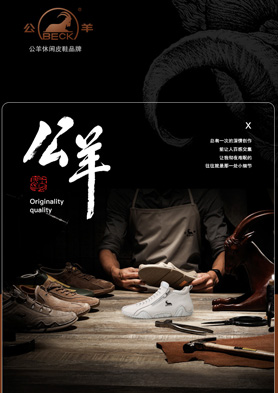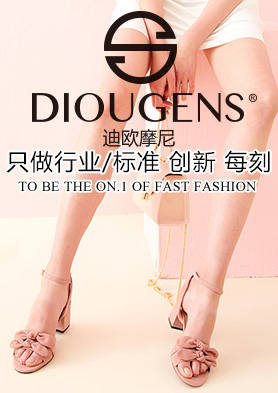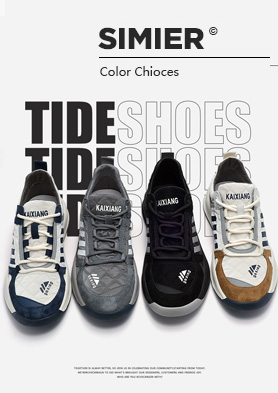鞋话
旧时代的妇女,从当姑娘起,便应该学会纳鞋底,做鞋,幼时为父兄做鞋,婚后为丈夫做鞋,老了给儿孙做鞋。仿佛妇女为做鞋而活着。
战火纷飞的国共内战时期,青年壮丁仓促离家走上前线,妻子灯下哭道:“临走也没来得及带走我刚做的一双鞋!”
我少年时听过孟姜女唱词:
我夫一去十载整,
一双新鞋未穿成,
我今做鞋二十双,
一年两双把夫寻,
不见不回还!
台上的孟姜女唱,我坐在下面掉眼泪,旁边有人笑我神经病。“你这是弹琵琶掉泪,替古人担忧啊!”
我初到澎湖马公,年少无知,在街上路摊买了一双美军大皮鞋,八成新,五十元,那时每月薪饷才三十五元,穿上皮鞋参加集合,惹得全场官兵笑成一团。
我的亲大妈耶,张放穿的是两条运输舰!
哈哈!你这双大皮鞋是麦克阿瑟扔的吧?
我穿了半小时,便藏了起来,许多人前来探求究竟,想以低价收买,我留着也没用处,根本无法穿它出门,结果以二十五元卖出,换了一双新的回力A球鞋。
我穿了大半辈子的鞋,不论布鞋、胶鞋、球鞋、皮鞋,甚至草鞋或木屐,最舒服而合脚的则是旧鞋。每次穿新鞋,我的两只脚总被挤得红肿数日,有时还会流血受伤,直到新鞋穿习惯时,才能走路平稳。
有一年出国,去菲律宾,因有虚荣心,买了一双新皮鞋,在马尼拉走了三天,两只脚被磨得患了蜂窝组织炎,成了瘸子,最后买了一双球鞋,穿回台北进医院。
田间有一首抗战诗《鞋子》,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回去, 告诉你的女人:
要大家 来做鞋子。
像战士脚上穿的 结实而大。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众人熟睡我独醒。别人鼓掌我撇嘴,我冒昧地为诗人改诗:
回去, 告诉你的女人,
让她做鞋子;
别磨脚呵! 别起泡呵!
穿鞋跟交朋友一样,老朋友总比新朋友好,因为脾气了解,性格清楚,老朋友聚在一起心情坦荡,没有顾忌,老年人比小伙子有经验,有学问,能够增广知识见闻,别听年轻人胡扯八道,他们写的“火星文”日新月异,连他们自己也看了莫名其妙。你交这些“朋友”有屁用?我的牢不可破的固执观念:“这一代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你别把幸福寄托在他们身上。”
打开电视机,总是那几个年轻男女在耍嘴皮子,专家像鞋店的新鞋,刚下飞机来台北,就能够指出淡水河的整治方案、歌仔戏的发展路向,以及整修捷运系统的具体做法,我有时想:如果法国巴黎召开巴尔扎克作品研讨会,总不会把李远哲先生请去作专题演说吧?但是李博士虽是化学专家,他在台湾可以修水利、谈经济、办教育,主持两岸交流,甚至练军队、造战舰……这毛病是科举制度的余波,只要得了诺贝尔,就可以纵横天下,成为现代圣人。咱不信这一套。
鲁迅认为“博学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专家“悖在倚专家之名,谈论他们所专门以外的事。”再加上咱们的媒体从业人员“总以为名人的话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记者向人家请教,人家不得不站出来讲话。若是台湾记者如此落后,我倒盼望各大学取消新闻传播学系,因为这门科系非但无益,反而为社会制造麻烦,我的这项建议或许有人质疑反对,但再过十年,说不定有人赞叹我的宏观眼光。不信,等着瞧吧!
- 上一篇:喜欢平跟鞋
- 下一篇:战疫·秀洲丨小红鞋完成了使命 但抗击疫情的脚步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