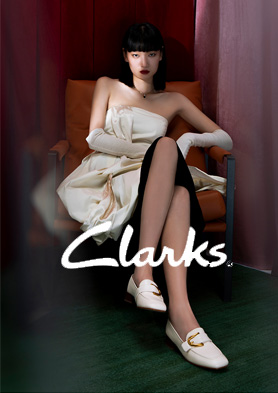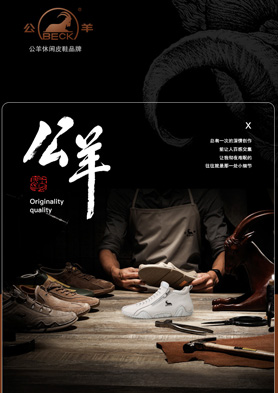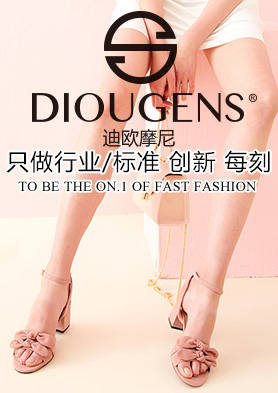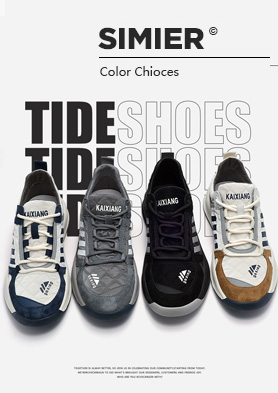鞋子的“烦恼”
7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是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长大的。包括单鞋和棉鞋,母亲在一年里要给我做两或三双布鞋。如果哪双鞋,穿一年半载后变小了,也不会扔掉,还要给弟弟接着穿。
穿着母亲缝制的“千层底”,1988年上完了小学,进入了初中。这时,同学中除黑色的“千层底”和黄色的解放鞋之外,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白色回力鞋。虽然母亲的布鞋做得很精细,鞋底的针脚细细密密、鞋面的布纹匀匀称称,穿在脚上既好看,又舒适。但与回力鞋相比,灰头土脸的“千层底”便相形见绌了。于是经常看着班里同学的回力鞋,想象着自己何时也能穿上回力鞋;想象着自己穿上回力鞋,是什么模样、什么感觉。当时,为自己不能拥有一双漂亮的回力鞋,苦恼了一阵子。
1990年春天,学校举行一年一届的春季运动会,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短跑。谁知,由于起跑速度过快,脚上原本有些松垮的布鞋一下子飞了出去。一时也顾不了许多,只穿着一只鞋坚持跑到了终点。然后追着记分的老师,在确认自己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后,才光着脚在跑道中捡回了那只甩落的布鞋。学校运动会后的第二个月,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镇里的运动会。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既兴奋、又郁闷。难道还要穿着这双布鞋到镇里“献丑”吗?终于在一个亲戚家借了一双回力鞋,风风光光地参加了运动会。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村子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1990年秋,父亲也利用农闲时节,在附近村里收购怀药,再与其他人合伙贩运到外地,赚了些钱,家里的条件方有所好转。特别是当年冬天,一次可能是赚了2000多元。返家途中,给我捎了一双回力鞋。紧攥着那双鞋,当时激动不已,也让多年捡我旧鞋穿的弟弟羡慕不已。晚上特意把它放在了枕下,一觉到天明。
没有鞋时,格外的想;有了鞋,却舍不得穿。“过年时再穿吧”,几乎每天要打开柜子看一眼、摸一下。当时想,如果有两双回力鞋该多好。一双今天就穿,一双留待过年。
终于“珍藏”了近两个月,在大年初一清早,才郑重其事地穿上了新鞋。这双回力鞋,一直到1992年上高中时,又小又破,实在不能再补,才彻底“退役”。
1993年,也是春节前,母亲给我买了第一双皮鞋。说是“皮”鞋,其实是乡村集市上最便宜的“人造革”。1998年,是在郑州工作的第一年,月工资800元。半年后,稍有积蓄,便在二七广场一家商场内买了一双真正的名牌皮鞋,记得很清楚,220元。
转眼间,在郑州工作十年了。十年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材质不同、款式各异、价格不等的鞋子,足有10多双,摆满了鞋柜。
20年前、15年前,每当外出时,常为没有鞋穿而烦恼;而今天,出门时,也有烦恼,常常为不知该穿哪双鞋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