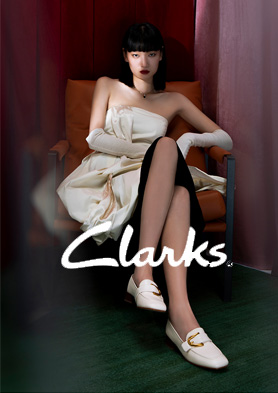梦回珠穆朗玛 —— 珠峰南坡攀登全纪实
本文作者 暮秋 ,一位旅美华人,也是一位热情的山友,曾攀登过珠峰、卓奥友等8000米山峰,本文就是他2009年跟随罗塞尔登山队从南坡登顶珠峰的纪实性登山报告。文中详细的介绍了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详细过程,非常值得一读,特在此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脚跨世界之巅,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面罩上的冰,然后紧抱着双肩以抵御寒风,茫然凝视着广袤无垠的中国西藏。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只觉得脚下绵延的大地是如此壮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憧憬着这一刻的豪情满怀。然而现在,我真的站在这里,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却提不起一点力气来感慨抒怀。”这是《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的开场白。许多年前读此书时,我就冥想着作者所描述的场景和感受。2005年站在珠峰脚下时,我又为珠峰的雄伟壮丽所震撼。此后难以忘怀,终于在2009年春随罗塞尔登山队从尼泊尔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走向神山
去珠峰要先从加德满都飞到一个叫卢克拉的小山村,然后向北徒步八、九天才能到达。大约五千万年前,北漂的印度板块就是在这里撞到并插入亚洲板块,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大地在撞击地带陡然从海平面升到世界之巅,旖旎的风光像仙境般的如梦如幻。徒步头几天,山路在林壑间蜿蜒曲折,头顶是挺拔的雪山,脚下是幽幽的峡谷。大片的白云像缎子一样闪着亮光,凌空的落瀑像飞虹般的洒向谷底。海拔5000米以上,四周只剩下石头与冰雪。珠峰南坡的雪山和北坡看到的很不一样。雪山一般都是拔地而起的,像刀一样地直刺青天。
在这段路程的最后一段,两旁渐渐出现了一座座玛尼堆,那是攀登珠峰遇难者的石冢。在一个小山村旁的一个山坡上,我找到了霍尔(Robert Hall)的石冢。霍尔是1996年珠峰著名山难中的两个领队之一。当年山顶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雪于一夜之间夺去了几位登山者的生命。霍尔因不肯丢弃他的队员而留在了山上,最终在南峰顶遇难。霍尔石冢面对雪山伫立着,几米以外是遇难队员的另一座石冢,两座石冢由一条彩旗连接。周围没有人,也没有喧嚣。只有太阳从云间射出一束束光芒,寂静无声地照向大地。
珠峰大本营海拔5300米,建在山谷的尽头。谷底是条十几公里长的冰川,冰川里是成千上万的冰塔。早上阳光明媚,彩旗在微风中轻抚着道道晨光,冰川在山影里泛出淡淡的幽蓝。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幅透明的水彩画。白天营地里人来人往,热闹异常,队员们或读书,或聊天,充分享受着高原的阳光。而当夕阳西下,日照金山,山谷下方就会涌上大团的云雾,瞬息之间令气温骤降,暮色降临。我特别喜欢喜马拉雅山的夜色。月亮升起前,四周黒虚虚的,伸手不见五指。伫立在黑夜之中,望着天上的寒星点点,听着谷中的隆隆冰崩,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
顶峰之路
南坡的登顶路线从下到上分为四段:(一)昆布冰瀑(二)西冰斗(三)洛子面(四)南山脊。若想对这条路线有个感性认识,最好的办法是逆着攀登路线从上到下对珠峰南坡的地形有个了解。珠峰峰顶象金字塔一样共向外伸出三条山脊,其中向南伸出的叫南山脊,这是攀登路线中的第四段。南山脊与南面比邻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海拔8516米)在海拨7950米处相接,形成一块马鞍形的平地,叫南坳。仿佛商量好似的,珠峰与洛子峰平行向西各自伸出一条几公里长七千多米高的山脊:珠峰西面的叫西肩,洛子峰西面的叫努子峰。于是夹在西肩与努子峰之间形成了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山谷。山谷东端(海拔6400米)止于南坳正下方,两者之间的冰壁叫洛子面,是攀登路线中的第三段。山谷本身叫西冰斗,是攀登路线中的第二段。在西冰斗的西端(海拔6100米),山谷突然变窄下垂,形成一个800米落差的断坡,直落到谷底的珠峰大本营,这段断坡叫昆布冰瀑,也是攀登路线中的第一段。
昆布冰瀑是珠峰攀登史上夺去最多生命的路段。千万年来,西肩、洛子峰、与努子峰上的冰雪最终都会聚到西冰斗,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缓慢西移,挤入狭窄的昆布冰瀑,再落下800米后注入昆布冰川。这是一段活的冰瀑,每天下移一米左右。上百米厚的冰层在这里断裂,坍塌,变得支离破碎。深不见底的冰裂缝纵横交错,大到房子般的冰块东倒西斜。在冰瀑中蠕行的登山者,随时都要提防可能突然开启的冰缝和崩塌的冰塔。如果说对付冰缝和冰塔已让人头疼不已了,那高高悬在冰瀑两侧的浮冰才最令人恐怖。浮冰几十米厚,像斑驳的墙皮一样挂在上千米高的西肩和努子峰上。哪天随便掉下一块,上千吨重的冰层很快就会在岩壁上摔成齑粉,形成雪崩,然后重重地砸向昆布冰瀑。如果这时恰好走在其中被砸到,那绝无生还的可能。为了降低被砸中的几率,我们一般选择在冰块相对稳定的半夜快速通过。
我永远忘不了5月7日那一天。那天上午十一点左右,西肩突然发生了这季最大的一起冰雪崩。轰鸣的雪崩雷霆万钧,从千米之上滚滚而下,瞬间就砸向了昆布冰瀑。雪崩落地后扬起的雪尘经久不散,像朵盛开的白莲花覆盖了整个冰瀑。不久对讲机传来急促的呼救声,原来有三名队员在雪崩区失去了联系。所有的队伍马上行动起来,我们队也派出了6名精干的夏尔巴前往营救。从高倍望远镜中,我们看到营救人员从冰缝里救出了两名受伤队员,却怎么也找不到另一名夏尔巴。人们最后只找到了他被雪崩打掉的背包和一只靴子,而这名夏尔巴却被永远埋在了昆布冰瀑。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早早返回了各自的帐篷。帐外凛冽的寒风撕扯着乌云,惨白的月光不时透出云层照耀着雪山。我缩在睡袋里思绪起伏,一遍遍地看着相机里的雪崩录像。那绽开的白莲花是如此美丽,美丽得让人凄凉,教我不能相信就是它在瞬息之间吞噬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触及巅峰
登珠峰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首先要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三次上下山的拉练,让身体适应高海拔的环境;然后耐心地等待好天气;最后从大本营出发用五天时间登顶。由于大陆和海洋的温度差,地球表面会形成冬季由大陆刮向海洋和夏季由海洋刮向大陆的季候风。在8000米高空,强劲的季候风一般不适合登山。只有春秋两季在季候风转向时,高空才会短暂出现风力较小的几天。而喜马拉雅山的登顶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中完成的。毫无疑问,能否准确地抓住这个窗口是登顶珠峰的关键。我们的领队罗塞尔在这方面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罗塞尔已组织珠峰攀登十几年了,过去一直在北坡,今年才开始转战南坡。可他这次再次彰显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实力,精确无误地捕捉住了时间窗口。首先,他成功地抓住了5月5日这一天转瞬即逝的高空稳定日,让6名夏尔巴和一名队员率先登顶并打通道路。其次,他果断地叫停了5月10日的冲顶,避免了队员可能发生的冻伤。最后,当真正的窗口来临时,罗塞尔指挥他的队伍分两批于5月21日和23日成功登顶,而23日之后就再没有任何队伍登顶。
罗塞尔把我们22名冲顶队员分成A,B两组,给我们订下的计划如下。
第一天:登昆布冰瀑和西冰斗,到达洛子面下的二号营地(海拔6400米)。
第二天:在二号营地休整。
第三天:登洛子面,到达三号营地(海拔7300米)。
第四天:从三号营地到达南坳(海拔7950米)
第五天:从南坳登顶并撤回南坳。
第六天:下撤至二号营地。
第七天:下撤至大本营。
每一名队员在第五天登顶时都会有一名夏尔巴协作跟随。罗塞尔的夏尔巴团队实力极强,尤其是夏尔巴队长普巴扎西正值壮年,到2009年底共完成了15次珠峰登顶。普巴很友善,见到每名队员都能叫出名字打招呼。但最潇洒的还是他在寒风中带领夏尔巴工作的样子,那种玉树临风的大将风度让人顿感他才是雪山真正的主人。
5月17日凌晨2:30,我们A组从大本营出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夜色里罗塞尔和每一名队员紧紧握手祝福。正当我们大步迈出营地的时候,一轮明月从努子峰顶一跃而出。素月流天,四望皎然,周围群峰顿时像海底世界一样发出银辉。夜里攀登我们只需专注脚下,在昆布冰瀑里小心地绕过冰缝,攀过雪崖。一路上我们快速前进,几乎没有休息,终于在拂晓时分走出了危险的昆布冰瀑。这时黎明刚好来临,回首望去,晨曦中的冰瀑就像是海市蜃楼中的幻景。
在简短地休息一下后,我们开始穿越西冰斗。西冰斗地势平缓,本无难度。可当太阳升起后,我们却面临着炎热的考验。西肩、洛子峰、努子峰三座峭壁上的冰雪象三面巨大的镜子,把强烈的阳光聚集到西冰斗里。这里白天可以到达40度的高温,走在其中就像置身在放大镜的焦点下,酷热难熬。太阳出来前我还冻得发抖,可太阳出来不到五分钟我就开始一层层的脱衣服了。当我狼狈不堪地走过西冰斗到达二号营地时,早已头昏目眩,口干舌燥。顾不上道谢,我接过夏尔巴递上的水壶一口气喝干了两升水。
修整一天后,我们于19日开始攀登西冰斗和南坳之间的洛子面。洛子面由坡度为45度的冰面构成,刚好和泰山一样高(1500米)。登洛子面是对队员体力和冰爪技术一个很好的考验。几小时走在坚硬的冰面上一点也不能放松,因为万一滑倒脱离固定绳,那只能一滑到底,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夏尔巴和特殊情况下,一般登山者很难在一天之内到达南坳,都要在海拔7300米的三号营地过一夜。营地完全是在倾斜的冰面上砍出来的,即使在营地里走路也需把自己扣在固定绳上,因为以前曾发生过队员滑坠遇难的事例。
20日从三号营地出发后,我们基本上是在岩壁上攀登。今年是干燥年,冰雪比较少。冰爪踩在倾斜的岩石面上,发出类似金属刮磨陶瓷的声音,令人非常不爽。可这也让我们真切地看清了黄岩石带。黄岩石带曾是海底沉积岩,可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却把它托到了近8000米的高空,成为喜马拉雅山一条标志性岩石带,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现在造山运动还在继续,印度板块仍以类似指甲生长的速度继续插入亚洲大陆,据说再过几百万年整个尼泊尔都要插到西藏下面了。我们于午后到达了南坳。由于地处珠峰与洛子峰之间的交界点,南坳是个大风口。平流层像过风洞似的从这里无遮无拦地通过,不仅把地上的冰雪吹得一干二净,也把南坳以西的天空吹得晴空万里。南坳以下的云海中一旦有云团升过南坳高度,就会被风瞬息吹散,化于无形。
在南坳抓紧时间睡了两个小时。晚上11:30,夏尔巴尼玛准时来到了我的帐篷前。在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装备后,我们出发了。一路上队员们默不作声地向上攀登,头灯在漆黑的夜里像是天上垂下的一串珍珠,而下方不时发生的蓝色闪电却像藏在云层里的巨大游龙。天渐渐亮了,黎明的曙光在地平线上升起。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向上攀登时,眼前的白雪突然变成了绛紫色。回首东望,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几座山峰在浩瀚的云海上露出了峻峭的剪影。7:15我到达了海拔8750米的南峰顶。在这里向导埃德伦为队员换上新氧气瓶。我告诉他我的氧气面罩出了问题,经验丰富的埃德伦立刻判断出是通气口被冰堵住了。他说只要从外向里吹口气就可重新打通。由于通气口在面罩的嘴部和脸颊两个位置,他替我吹气时姿势自然引人联想。于是幽默的埃德伦“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这可不是在亲吻你!”就在我差点笑出声来之际,埃德伦已呼呼两口把通气口吹开了。一股清凉回到头上,感觉就像在水底憋了半天重新升到水面上一样。我和尼玛兴奋地击了下手掌,说了声:“出发吧,兄弟!”
在南峰顶可一览无余地看清后面的路线,出发后要先横切一段,然后再攀登最后一道险峻的山脊。山脊上的积雪被风吹出一个个巨大的雪檐,人在上面显得非常渺小。一小时后,我和尼玛来到了著名的希拉里台阶下。希拉里台阶是块大约两三层楼高的巨石,表面光滑,几乎直立,两侧都是上千米的峭壁。这是通往顶峰的必经之路,希拉里和丹增在1953年第一次登顶珠峰时几乎在此铩羽而归。正当我抓着绳索准备攀登时,台阶上面有一个队员探出头来,原来是有人登顶后开始下撤了。等那人终于下到了台阶底,上面却又露出一个人头。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我后面已聚集起几个等候的队员了。尼玛再也按捺不住,见第四个露头的是个夏尔巴,他立刻大声用夏尔巴语和他勾通起来。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结果是那名夏尔巴奇迹般地缩回了头。尼玛立刻从后面一拍我肩膀:“快上!”仿佛从梦中惊醒,我条件反射般地抓住绳索,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居然一鼓作气地登上了希拉里台阶!到了阶顶松下劲后,我才感到肺像炸了一样,竭力张合着却吸不进气来。骑在岩石上咳了半天,我才终于调匀呼吸回过神来。探头望望下面,只看得见尼玛的脑袋,想了半天也没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上来的。
等尼玛上来后我俩准备继续上路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原来希拉里台阶之上还要在岩壁侧面攀登一段。路宽不足一尺,一边是直立的岩壁,一边是暴露的悬崖,有点类似华山长空栈道上的臬臬椽。更要命的是上面还有几个等待下山的队员。让他们退回山上?不可能。让我们退下希拉里台阶?更不可能!一筹莫展之际,还是尼玛想出了一个办法:“从他们身外错身过去。”“什么?错身?在这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啊,而且身上还有厚厚的连体羽绒服和披披挂挂的装备。可我实在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开始和第一名队员错身。我先把扣在固定绳上的两个主锁松开一个,用一只手扣到那人另外一侧的固定绳上并牢牢抓紧,然后再慢慢伸出一只脚从他身外跨过,小心地踩到他另一侧的岩石上。这时我除了两手抓着固定绳和两脚踩在岩石上之外,整个身体都悬空挂在那名队员身外。那人很配合地一动不动,尽量把身体挤向岩壁。我小心地跨过另一只脚,移过另一只手。尼玛帮我松开那边的主锁,我赶紧把它扣在我这边的固定绳上,就这样完成了和第一名队员的错身。我和尼玛如法炮制地和几名队员错过身后,终于重新爬上了山脊。
从这里地势开始变缓,再没有什么难点了。向上走了不久,我终于真切地看到了珠峰峰顶:在白雪与蓝天的交界线处立着一小尊佛像,佛像旁边绕着许多藏式五彩旗,几名身着橘黄色羽绒服的夏尔巴在向我们招手。我和尼玛缓步向前,感觉是在空中漫步,一切都像在梦境里。强劲的平流层无声吹过,带走脚下一缕雪尘飘向远方。前方的路不再升高,眼前出现了广袤的西藏大地。5月21日上午8:50,在经过9个小时不停的攀登后,我终于迈上最后一步,站到了世界之巅。极目远眺,四周一览无余。上面是碧空如洗的蓝天,下面是波澜壮阔的云海。连绵不绝的喜马拉雅山万峰攒动,山舞银蛇。雪域高原在天地之间呈现出一派壮丽的风光。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尼玛突然向前扑倒,对着佛像深深跪下,朗声诵起了佛经。我被一股莫名的情绪感染,不由得也激动起来,双手合十随着尼玛拜了下去。
静水深流
两天后,当我走出昆布冰瀑返回大本营时,营地里一片欢呼,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原来是驻地人员敲着铝盆和塑料桶在热情地欢迎我归来。我心头一热,顿时有种“回家了”的感觉。走进营地后,他们与我一一拥抱祝贺。于是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敲锣打鼓地迎接每一位归来的队员。
夜里我和两名队友在餐厅帐里聊天,知道了吉姆所发生的意外。原来吉姆随B组出发后,在洛子面下突然犯病昏厥,遗憾地放弃了冲顶。吉姆五十出头,非常乐于助人,是我这次接触最多聊天最深的队友。吉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曾主动放弃快要到手的博士学位。这次他的一大心愿就是把母亲的遗像带到峰顶,所以对他犯病没能冲顶,我和队友都深深地感到遗憾。稍感宽慰的是B组队员最终替吉姆完成了心愿,把他母亲的遗像带到了峰顶。这时罗塞尔进来了。在经历了几个不眠之夜,成功地指挥队员登顶后,他显得很疲惫。和队员聊聊天也许对他是一种放松吧。聊着聊着,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罗塞尔话题一转,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虽然吉姆和大家一起欢迎队友登顶归来,但他心里其实并不好受。你们欢迎B组时先不要急着上去和队员祝贺,而是在后面陪吉姆多站一会,这会对他是个安慰。”想不到向来说一不二铁面冰冷的罗塞尔竟是这样的细心!后来在欢迎B组队员归来时,我们总会自觉而默契地留下一人陪陪吉姆。而吉姆一如既往的用力敲打着锣鼓,热情地笑迎每一位归来的队友。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营地里热闹异常。队员们在雪地里笑着,跳着,拥抱着。罗塞尔撑了把伞,静静的站在一旁,望着他的队员们欢呼。
一个人一旦把一项工作当成事业,就会对它产生热爱并力求完美。我觉得罗塞尔就是把他的登山队伍当成一项事业来经营的。罗塞尔今年膝盖作了手术,走路略有点颇。但营地里经常可看到他一瘸一拐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弯腰捡起地上的垃圾。有次我们问他心中的标准是什么?他回答道:“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撤营后,这里不留下人住过的痕迹。”的确,我们队所有的垃圾,包括人的大便,最后都被全部运下了山。罗塞尔的这种爱山情结反映在他对垃圾的处理上,反映在他对队员的态度上,反映在他对攀登的精益求精上。也使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长期困惑我的疑问:到底是什么精神感召着人们来到喜马拉雅山?希拉里是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但他的感召力其实是来自他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热爱。从1961年他建立了第一所夏尔巴学校起,他就不断地返回喜马拉雅进行公益事业。1974年,罗塞尔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就不由自主地被希拉里吸引,加入了建设医院的行列,并从此结下了与喜马拉雅的不解之缘。
由此我又联想到我的队友贝丽。贝丽是个爽朗的德国姑娘,几年前只身来到尼泊尔,协助郝蕾女士(Elizabeth Hawley)工作。郝蕾女士在登山界可谓无人不知,没人不晓。1960年,37岁的郝蕾来到了加德满都,从此留下致力于登山史的记录。每年登山季节,她跑遍加德满都的大街小巷,收集核实各个登山队的信息资料,建立了世界上最全的登山数据库。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郝蕾女士已把她生命中的五十年留在了加德满都,贡献给了她所热爱的登山事业。虽然一座雪山也没登过,但她这种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却深得登山界的敬重。我常觉得一个人因能力超群而得到别人的佩服并不难,但要赢得别人的敬重却需要一种人格的力量,而郝蕾女士的生命中就有这种人格的力量。如今她已年过八旬,又动了手术,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穿街走巷了。于是在加德满都的小巷里,又出现了德国姑娘贝丽的身影。加上另外三名志愿者和维持8000ers数据库的哲伽斯基,这些人继续默默无闻地延续着这项“平凡”的事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当生命的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时,就会积淀出一种深厚的感召力。那是浪花下深流无声的大河,云层上肃穆巍峨的山巅。于是有了希拉里,郝蕾,罗塞尔,贝丽……。正是这群人对山一点一滴的热爱,才汇成了一条静水深流的大河,使我们在喧嚣的红尘之上,还能看见一座庄严的山峰,找到一片精神的家园。
5月27日,下了两天大雪之后天气放晴。喜马拉雅山银装素裹,阳光普照。我们在洁白的世界中撤离了大本营。路过罗布其时,我和两名队友离开山路,踏着大腿深的雪找到了1996年山难中另一位遇难向导菲舍(Scott Fischer)的石冢。像以往纪念逝者一样,我试图捡起一块石头放在石冢上。然而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的,因为两尺多厚的白雪早已盖满了大地。在雪中摸索了几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一举动显得多余。这石冢其实并不是我所真正寻找的,它只是一个标记,引导我们去追寻一种永恒。那永恒也并不凝固在这石块中,它早已化于无形,融入这山上的清风朗月了。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我们后人不过是通过这些有形的石块在感受那永恒的精神罢了。于是我捧起一大团洁白的雪,放到了菲舍的石冢之上。
菲舍的墓志铭简单而朴实:“他的精神永生(His spirit lives on)”。
轻云蔽月,流风回雪。天籁无声,大道无痕。

- CURRY 12 "WHAT THE BAY" 鸳鸯配色发布,致敬湾区传奇与全明星荣耀
- 耐克全新品牌宣传片《不争辩,只争胜》,致敬女性运动员和运动的力量
- 奥康情人节礼物已送达!
- On 昂跑推出 Cloudsurfer 家族革新之作 Cloudsurfer 2 训练型跑鞋
- 高蒂女鞋GAODI情人节特辑 | 以鞋为礼,步步生爱
- 诺贝达女鞋ROBERTA DI CAMERINO来点水钻高端局
- 斯米尔
- Charles&Keith
- 骆驼服饰
- 啄木鸟包包
- 康莉
- 金狐狸包包
- 老鞋匠
- 唯聚时代
- 德尼尔森
- 莱斯佩斯
- 花椒星球
- 红蜻蜓童鞋
- 意尔康
- 途漾潮鞋
- 康奈
- 四季熊童鞋
- 沙驰
- 牧童
- 卡西龙
- 花花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