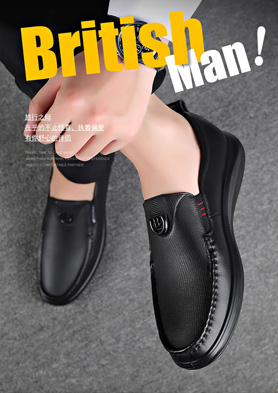一残疾少年擦鞋挣钱孝顺养父母
每天,当晨曦还未洒落大地,租住在乌鲁木齐市兽医站一处简陋民房里的马墩就已背起笨重的擦鞋箱,快步朝擦鞋地点——乌鲁木齐市友好大酒店后门奔去。
绝大多数时候,他眯缝着眼睛,眼巴巴地盯着来来往往行人的脚,却并不吆喝。他知道,自己的“兔唇”,即便吆喝,发出的声音也含混不清。但只要一有客人坐下,他就忙不迭地给人脱鞋,套袋子,一言不发地卖力擦起来,那股实诚劲,看得令人动容。擦完后,接过那一元钱,他才感恩地抬起头朝人家笑。
我像许多擦鞋客一样,早就留意起了马墩。在那些擦鞋匠里,他个子出奇地矮不说,脑袋还出奇地大,可是却有着孩子一般的小手小脚和纯真表情。可有时,影影绰绰又闪现出一种成人的凝重,这不禁让人疑惑起他的实际年龄。
7月6日傍晚,久燥的天空飘起了零星的雨滴。看到马墩孤零零地守在墙角等生意,我忍不住坐在了他的摊位前。
对我的询问,这个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擦鞋郎有一说一,只是很少看我的眼。
他说他17岁了,只有1.1米高,老家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农村,2003年随老乡来乌市擦鞋。他有一个早嫁的姐姐,在广州打工,年迈的父母后来也随他来乌市,在附近的巷子拾荒。
个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生长的,马墩并无确切的记忆。反正年龄是在一天天增长,身高却丝毫没变。后来家里实在太穷,加上病痛的折磨,仅小学一年级就上了好几年的他不得不辍学了。
“在乌鲁木齐好,有钱挣,比在老家干农活不知好上多少倍。”马墩说起话来,嘴有些漏风,但仍然透露出小小的骄傲:“就是老被人赶来赶去不好,可现在我敢耍赖了,他们赶不走我,每天我都能挣个一二十元呢。”
房租每月240元,再加上父母和自己的伙食开销,一家人每月大约需要花费五六百元,这些钱几乎全是马墩赚来的。他每天在街头擦鞋,凉皮、馕饼,什么便宜吃什么。冬来暑往,个子显得更小了,可擦鞋的脚步从未停止。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找到了正在附近拾荒的马墩的父母——父亲马宝田,母亲李搬,想告诉他们马墩的懂事和坚强。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听外人的安慰眼圈就红了。怎么也没料到,他们道出一个令我吃惊的事实:马墩是他们捡来的弃婴。
当年,老两口在13岁的儿子猝死后捡到了先天唇裂的马墩,几次手术,债台高筑也没治好马墩的唇裂。四五岁的时候,马墩脖子上又长了甲状腺瘤,做手术割去后,他就再难长高。这些年,花的钱可以盖3间平房,也没能让马墩恢复正常。
不知这孩子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反正孝顺得没法说。李搬一口气说了好几件事:家里拾来几部旧电视,看看就没影了,为解父母寂寞,马墩每天起早贪黑地擦鞋,硬给父母买了个新的电视机。“他那么小的个,每天还围着锅台弄吃弄喝给我们。”李搬有些哽咽:“我有高血压,这孩子一回家,就经常给我按摩脑袋,说是舒筋活血,长长寿寿,这么孝顺的儿子,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天上的雨滴渐渐多起来。再转身搜寻马墩的身影,他依然固守擦鞋箱前的那个小马扎上。父亲马宝田远远地朝他喊了一嗓子,要他回家,他应了一声,身子依旧没动。马宝田说:“我们也在想办法挣钱,好给孩子治病。这孩子很努力,他既想照顾好我们,又想多挣点钱去医院做唇裂手术,他想清楚地说话,想再长一点个子,更想读书识字找个好些的工作。这孩子个子不高,但心气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