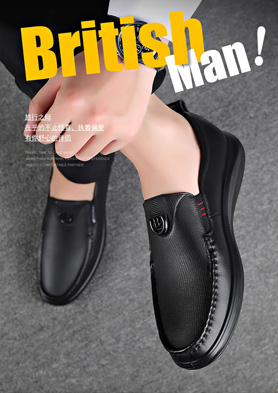艰苦的白球鞋与昂贵的童鞋
30年前我7岁,随奶奶从海拉尔到叔叔所在兴安盟突泉县生活。当时叔叔在一所我已忘记名字的乡小学教书,便把我带到学校里去适应环境。
这引发了我平生唯一一次的罢课行径。
记得第一天的第一节课后,我便被同学们围拢在中间。他们带着惊诧的眼神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主要议题是我脚上穿着一双簇新的白球鞋。他们弄不清爽我为什么要穿着鞋来上课,在他们眼里鞋是上城、过年或串亲戚时才派上用场的。于是他们抬着满是黑皴,有的还裂着口子的脚和我的白球鞋比照,仿佛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异类。短暂的惊诧后,他们觉得再无兴味,便一股脑地涌出教室到后山玩去了,只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那里。而我这个“异类”对他们也没有丝毫的认同感。一天过后,任凭叔叔如何威逼利诱我再不踏进他学校大门半步。
虽说是城里孩子,其实我与我首届农村同学相比,优势也仅一双鞋而已。因为家境贫寒,那双白球鞋我穿到小学三年级,鞋面被大拇脚趾头抠出两个大洞,鞋底磨得能瞅见太阳时才不得不扔掉。之所以舍不得,是因为这双鞋曾为我立下过大功。有一次学校组织鼓号队,要求学生品学兼优外还得有一双白球鞋。我的那双白球鞋早已失去了本色,变成灰的了。我就偷偷地用白粉笔把它蹭白了去报名,居然过关了。
再大一点,我就逐渐全面接管了父亲的劳保鞋,什么黄胶鞋、翻毛鞋、大头鞋,我统统穿过。只有一双“三接头”皮鞋,父亲不让我碰,那是他出去撑门面的。但我还是背着父亲穿到学校显摆了一回,结果招致一顿胖揍。
初二时候,妈妈下狠心给我买了一双我梦寐以求的“回力”牌白球鞋,就是有些大。我38号的脚,妈妈买的是40号的鞋,理由是这样能多穿几年。尽管我把鞋带系得紧紧的,脚脖子都不过血了,脚丫子还是在鞋里面直咣荡。穿着这样的鞋不仅使我走起路来象鸭子一样蹒跚,而且鞋里面还发出“咕唧、咕唧”的声响。同学们向我咨询买大鞋的原因,我颇有市场前瞻意识地自嘲说:“听说鞋要涨价了。”
两双白球鞋定格为人生值得回味的片段,也左右着我的穿戴观念。我把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的一段话当成座右铭。记得那句话是这样说的:衣着不论新旧,只要干净整齐,表现出人的精气神就好。
对我的穿着信念,老婆和儿子一致地嗤之以鼻,他们共同的评价是,我是“屯里来的”。儿子刚刚9岁,衣服就塞满了家里的两个大柜子,床底下也堆满装着他鞋的鞋盒子。一年里面,什么季节儿子该穿什么,老婆规划的井井有条。如此调教之下,只要衣服、鞋有点脏旧,儿子就拒绝往身上套,理由是“丢份”。
面对这样的景况,我一向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一双两个底、几根带子的儿童凉鞋要卖300多块。儿子只穿了一夏天就因为小了而弃若敝履。
我在对儿子脚丫子的生长速度表示赞叹的同时试着同老婆探讨:“以后给儿子买鞋能不能买稍大一点的?”
“你不知道鞋的号码不合适影响孩子的脚发育呀?”
对鞋的大小到底能对人的生长发育造成多大影响的科学依据我不甚了了,因此老婆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使我继续保持着“屯里来的”的本色。
一天,边看电视边闲聊时,儿子跟老婆“套词”:“妈妈,日本人发明出了能象蜘蛛侠那样爬墙的鞋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一双?”
“你要那样的鞋干什么?”我插话问。
儿子嗫嚅着不肯回答,再三追问之下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是考试考不好,穿着那样的鞋爬上楼,你就打不着我了。”
我直接晕倒。
- 上一篇:我和绣鞋垫的女孩情史
- 下一篇:战疫·秀洲丨小红鞋完成了使命 但抗击疫情的脚步不会停